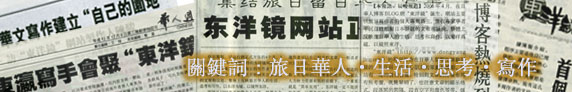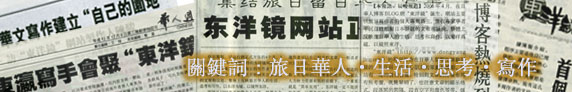章子怡在日本拍了一部电影,叫《御狸殿》,扮演的角色是狸姬。这个狸,日本读作tanuki,有人说那就是中国的狐狸,也有人说是狸猫,到底啥东西呢?
据日本人考证,狸,通观中国古籍,乃是指山猫之类。明代《本草纲目》说狸有数种,其大如狐,头圆尾大的叫猫狸,好偷鸡鸭,此外有虎狸、九节狸、香狸等。日本人从中国拿来了狸字,可四下里一找,日本没山猫,对不上号,就把这个汉字派给长相差不多的tanuki。这种事多了,难怪我们在日本遇见自家的汉字也不知所云。17世纪后半落户日本的朱舜水辨认狸和tanuki不是一回事。中国也有tanuki,就是那一丘之貉的貉。寒冬时节,tanuki肉加牛蒡做酱汤,日本叫狸汁,而章子怡的狸姬来自大唐,说中国话,就成了貉子汤(貉,he也,但貉子,应该念haozi)。僧人吃狸汁,用魔芋顶替tanuki。狸是猫科动物,tanuki(貉)腿短尾粗,脸圆吻尖,是犬科的原始性动物。据说貉肉腥膻,而广东人善吃,前两年把果子狸吃出了大名,想来那才是美味。日本有一种汤面叫狸荞麦面,其实和狸(以下指tanuki)不沾边儿,大概先有狐荞麦面,又编出狸荞麦面。狐狸不分家,狐迷人,是狡诈的形象,狸装相,像我们的猪八戒,傻乎乎有君子之风。它短粗胖,不利于行,受惊会装死,过一会儿才起身脱逃。皮毛可贵,但是还没捉到狸,先就算计做皮袍子,这样打如意算盘日本就说是皮算用。
关于狸,日本有很多传说,是民间故事的主角之一,三番五次被搬上银幕。过去狸出没于土仓寺庙,如今已不易见,常见的是信乐窑烧制的陶狸,立在酒家门口,姿态倒像是企鹅。如图,三狸待沽,摄于陶瓷店货架。信乐在滋贺县,一千多年前朝鲜半岛人渡海而来,带来了烧陶技术,是日本六大古窑之一。战后的一九五一年昭和天皇巡行到此,信乐窑陶狸摆放了一路,拿着小太阳旗欢迎,天皇一高兴就吟了和歌,从此这东西遍布四岛。
陶狸的基本形象是头上戴斗笠,一手拎酒壶,一手拿帐本,这个造型据说是一个叫藤原铁造的陶匠上世纪中叶创作的。十七世纪初日本酿造出清酒,当老子的晚上要喝两口,就叫儿子去酒店打酒。拎着酒壶,拿上折子,那时打酒是赊帐。打酒戴斗笠,大概闷在家里喝酒往往是雨天,况且斗笠是信乐特产。酒家用提子从酒坛里舀出酒,灌进细细的酒壶,酒钱记在折子上。我小时候见过打酒的情景,好像中国不是用折子,酒债寻常行处有,像孔已乙那样就把名子记在店里的粉板上。
信乐陶狸似没有狸姬,都拖了一个大阴囊,这也是有传说的。文字最早见于十七世纪末的《本朝食鉴》,说狸进了村,坐在炉边,偷偷烤火,暖乎起来就展开阴囊,长四、五尺,包裹小孩。阴囊,日俗称金玉,狸用来害人的金玉不是立体膨胀,而是像延展金箔,好大的一片。京城的狸下乡到江户,吹牛说∶咱的金玉铺开来可不止八张榻榻咪,比十张还大哩。乡下的狸反驳∶胡说,应该是八张大小。狐在一旁插嘴∶是十张,是十张,人家是按京城的榻榻咪来算的。原来关东与关西榻榻咪尺寸不一样。人类崇拜过男性生殖器,对象是阴茎,至于阴囊,在情人旅馆门前立一狸,再铺张也不管用。
中国古话有鼓腹,日本人将其反过来,指实到狸身上,说它月夜敲打腹鼓作乐。狂言有一出《狸腹鼓》∶夫狸不归,身怀六甲的妇狸化作尼姑出门寻找。遇见猎人,尼姑告诫他杀生罪孽深重。猎人悔过,但走狗狂吠,尼姑被看破真相,亮出腹鼓求饶。妇狸敲打腹鼓,乘机夺过来弓矢,猎人落荒而逃。铁匠用狸皮做风囊,陶狸那穹窿也似的肚子来自风囊一鼓一鼓的联想也说不定。这么一来,有如一钵千家饭、孤身几度秋的布袋和尚,功德圆满,更招人喜爱。但腹鼓这件事到了物理学家兼随笔家寺田寅彦的笔下就别有意思了∶
从前就有很多人相信朦胧月夜狸敲打肚皮。问老人们,有好几个人说听见过。从诗意来说,确实有趣味,至少可以写俳句。但狸真的玩那个把戏吗?听见过声音的人很多,但追究一下发出那声音的“根源”,说真的看见狸把肚皮当作鼓敲打的人很少有。那么,为什么认为远远听见的嘭嘭嘭的声音是狸发出的呢?听见了声音,也没有证据说不是狸,但是从其他角度来考虑,就不该相信那种事。说是狸的证据好像更没有。如今一本正经地议论这种事,也许有人要生气,认为是愚弄人。可是,认真考虑一下,世上相信没有证据、至少没有物质性证据的事情的人有很多。不,简直没人不相信。除了极端怀疑事物的哲学家,都相信像狸腹鼓之类的事情,坦然不疑。宗教家相信各种各样的神而且很多场合是相当物质的、具体的神的存在;很多科学家不怀疑法则的绝对普遍性;很多经济学家以自己在书桌上杜撰“人”的存在为基础高谈阔论;伦理学家各自拿随便制造的标准论说善与恶;艺术家从自己随意选取的立场夸夸其谈艺术的本质。我们眼见耳闻的世界种种也都跟狸腹鼓一样,追究这些的“根源”的人好像还没有。读近来流行的各色社会学家的论文什么的,尤其加深了这种心情。(2005/8/21)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