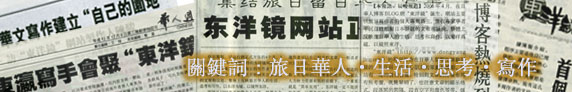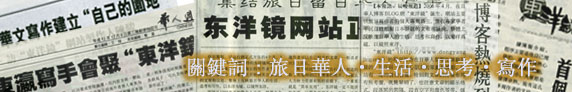时常看见一张老照片,是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与日本昭和天皇的合影:高大的麦克阿瑟一身便服,没有系领带,双手掐腰,身穿大礼服的天皇站在他一边,扬着小胡子,又瘦又小。这是日本投降后的9月27日。天皇陛下为命运惶惶不可终日,他的忠实臣民已开始抢购《日美会话手册》,这本只有三十二页的小册子畅销三百六十万册,创造了战后出版史第一奇迹。天皇到美国大使馆拜会麦克阿瑟,交谈三十五分钟,合影留念。谈了些什么,天皇至死不说,麦克阿瑟回忆:给天皇点烟时我发觉他的手在颤抖。天皇说:我对国民进行战争时在政治、军事两方面采取的所有决定及行动负全部责任,为此来拜访,把自己交给你所代表的诸国裁决。这一瞬间,我觉得面前的天皇是日本最好的绅士。手握铁锤似的烟斗,麦克阿瑟从此对天皇改变态度,不同意追究其战争责任。独领战后思想界风骚的丸山真男说,日本人在报纸上看见这张照片,彻底失去了自信。
三个多月后的1946年1月,天皇下诏,宣布自己不是神。同年,鲁思·本尼迪克特在美国出版《菊与刀》,1948年日本翻译出版(本文的引文据日译本转译)。当时,日本不了解美国,不了解美国人,满怀疑惧,也许要扼腕奇袭珍珠港之前怎么没想到写一本“鹰与原子弹”什么的。政府指令各地开妓院,迎接美国大兵,并晓谕女人们,穿着检点,万勿在人前坦胸露乳,但美军进驻就下令废除公娼,真搞不清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对于日本人来说,切身之所急,急急如律令,不会是从镜子里观看自己的嘴脸,而是千方百计认识他们曾骂作鬼畜的美国人,所以《菊与刀》有如及时雨,写的是日本人,但处处比照美国人,正好拿来当教科书。况且史无前例地给日本文化抽象出一个模式,与美国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相提并论,更叫日本人惊喜,甚而鼓起了被那张照片打垮了的自信。
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家,写作《菊与刀》的基本手法是现场调查与比较研究。她不曾踏上日本,所谓现场是从侨民、战俘听来的,从书本、电影看来的。写日本无须身临其境似乎是美国人的绝活儿,“蝴蝶夫人”把艺妓张扬全世界,原作者也从未见过日本。本尼迪克特居然采集了这么繁多、琐碎而真切的生活细节,读来几乎有应接不暇之感,怕是日本人也未必写得出,叹为观止。不过,正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,到了国外更爱国,人们往往在记忆中不由自主地强化远去的事物,美化以往的一切。《菊与刀》是探究日本其国其人的经典之作,我们迟了五十年才移译,也不可急急于赶时或汲汲于应景,经典要当它是经典,最好由研究者操刀,用注解指出问题所在,如日本军队不使用敬语之类,以免误咱国人。当年日译本问世,一些日本学者起而攻之,其中固不乏感情抵触,但毕竟是他们家里事,总该看得更明白。日本人说的就不爱听,偏要站在美国人一边,这书就读得没意思了。本尼迪克特进行比较时,莫怪日本人抱怨,是以美国人完美无缺为前提的。
“我们要努力理解日本人的思想习惯、感情习惯以及这些习惯被注入其中的铸型(模式)。”于是,我们的本尼迪克特通过恩情义理等解析日本人的思想与行为(蓦地想起:什么什么思想与行为,这个说法出自丸山真男笔下,一度成为流行语。有趣),论断日本文化是耻文化类型。日本人津津乐道这个耻文化,至今不失新鲜感。本尼迪克特说,“运用人类学研究各种文化时,重要的是区别以耻为基调的文化和以罪为基调的文化”,可见,这是把日本文化归属于以耻为基调的文化,并非特别由日本文化归纳出一个独特的人类文化类型。就耻感或知耻来说,作者从日本文化中发现的基本是中国的儒教观念,只是日本人没有把“慎独”学到手罢了。我就想,倘若把这部书输入电脑,再把日本人变换为中国人,说不定我们也可以一读到底,当然也会像好多日本人一样提出异议。“耻”文化模式后来竟成了“模式”,论客竞起,都试图用一个字论定日本,如“甘”,如“缩”,如“侍”,见仁见智。
如书名所示,贯穿全书的,也就是贯穿日本人思想与行为的,是菊与刀的矛盾,即二重性。作者说:“菊与刀都是一幅画的部分。日本人极具攻击性,同时又老实;尚武又唯美;踞傲不逊又彬彬有礼;顽固又富于适应性;温顺又厌烦被人驱使;忠实又不可依赖;勇敢又怯懦;保守又欢迎新事物;他们非常介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的行动,同时,自己的劣迹不为人知时也深受罪恶感折磨;日本兵被彻底训练,却还是不听话。”(日译似有误,此处参考英文版翻译)说来我们古人早就看出日本人具有二重性,例如唐人包佶写诗送日本国聘贺使晁衡东归,有云:野情偏得礼,木性本含真。1937年周作人管窥日本,说:“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,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,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。日本人最爱美,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,不知道为什么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。日本人又是很巧的,工艺美术都可作证,行动上却又那么拙。日本人喜洁净,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,但行动上又那么脏,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。”
为什么日本人做事是二重的,两面的?本尼迪克特认为这种矛盾产生于他们小时候所受教导的不连贯性。像漆器一样,岁月给日本人涂上一层层漆,但是,“他们是自己的小世界里的小神的时代,甚至能尽情撒娇的时代,似乎任何愿望都能够实现的时代,在他们的意识中还留有深深的痕迹。由于二重性如此之深地扎根在心里,他们长大成人以后”,便表现出“既沉迷于浪漫的恋爱,又易如反掌地无条件服从家里的意见。既沉湎快乐,贪图安逸,又为了完成极端的义务而无所不为”之类的现象,令西方人瞠目。其实,我们中国人对此也瞠目。究其原因,我以为是历史进程造成的――日本刚刚走出原始社会,旁边已备下一个过于发达的中国文化,兼收并蓄,结果就弄成了这个样子。汉字与假名并存,语言的二重构造对二重性格的形成尤具有莫大影响。兔子急了也咬人,个人乃至民族都具有二重性。丰子恺说:“我自己明明觉得,我是一个二重任格的人。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、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、虚伪的、冷酷的、实利的老人(我敢说,凡成人,没有一个不虚伪、冷酷、实利);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、热情的、好奇的、不通世故的孩子。这两种人格,常常在我心中交战。”不过,日本二重性自有其特色,那就像他们的书刊既有横排又有竖排一样,是摆在明面的。诚如《菊与刀》所言,“日本人能毫无精神痛苦地从一个行为转变到另一个行为”。上班西装革履,下班又坐卧在榻榻密上,既拼命工作,加班以至过劳死,又尽情喝酒唱卡拉OK,不遮不掩,丝毫没有远庖厨的念头。倘若在中国,过去竖排是过去,要改为横排就一律横排。我们的二重性是阳一套,阴一套,当面是人,背后是鬼,满嘴仁义道德,满肚子男盗女娼,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不一样,另一面隐藏着,看上去只是一面,道貌岸然。中国人在二重之间有追求,追求中庸,统一,虽然终归是心向往之罢了。日本的二重性行为是并列的,不会在心中交战,不会像周作人那样“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”。周作人终于没看出日本人把二重性并列于外,说:“我们要觇日本,不要去端相他那两当双刀的尊容,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,虽然军装时是一副野相。”把野相看作表面现象,把吃茶弄花草看作本质的真面目,结果周作人就跟着一副野相的人吃茶去了。
每当看见麦克阿瑟与天皇的合影,就油然记起这位老兵的话。他说: “要是用现代文明来测定,我们四十五岁,日本人就像是十二岁的少年。日本人能接受新模式、新思考,给日本灌输基本概念是可能的,他们天生具有灵活接受新概念的素质。”当年在处理日本上美国很有点大人样,日本也真像孩子一样听话,顺从大人的霸道,但孩子会长大,而且暴富,对美国大人就开始说NO,似乎尤其有杀父情结。从二重性来说,这是日本人本来具备的,小荷才露尖尖角。
|